Abstract:
Based on the scale of time of Heqing core confirmed by astronomical tun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urve of carbonate content of Heqing core with that of the deep sea δ
18O and the loess grain siz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rbonate record of Heqing core is earlier than deep sea δ
18O record and the grain size record of the continental loess during the mid-Pleistocene revolution, meaning that the uplift of Tibet Plateau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mong the mid-Pleistocene revolution. Further, the curve of the carbonate content of Heqing core corresponds well with that of the deep sea δ
18O, reflecting that the change of the global ice volum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southwest monso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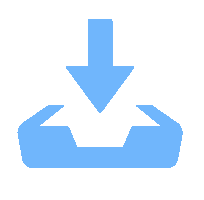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