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UR-FILL ADJUSTMENT OF THE TRUNK OF QINGSHUIGOU CHANNEL AND THE RESPONCE TO FLOW-SAND REGIME
-
摘要: 通过分析黄河口利津水文站1950-2006年水文、泥沙资料和1976-2006年利津至清7河段固定断面资料,结果表明:清水沟流路行水以来,进入河口区水沙通量总体偏低,来水来沙更集中于汛期,尤以泥沙量为甚,水沙搭配也较以前畸高;河口河道主槽淤积明显,且绝大部分淤积在CS7-清7河段,全河口段共淤积泥沙量为3.15亿m3,其中汛期淤积1.12亿m3,非汛期淤积2.03亿m3;河口河道主槽冲淤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即汛期强烈淤积、非汛期适度调整(1976-1979年),汛期强烈冲刷、非汛期强烈淤积(1981-1985年),汛期与非汛期持续淤积(1986-1996年),以及汛期冲刷、非汛期淤积(1996-2006年),并有2年期的"记忆"效应;河口河道主槽冲淤量与径流量、输沙量和来沙系数存在部分线性或秩相关,但来水来沙数量和水沙搭配参数并非为影响主槽冲淤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水沙过程、河床边界条件和人类活动干预等因素在主槽冲淤变化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Abstract: Daily observation data on river flow and sediment charges at Lijin hydrological station during 1950-2006,and fixed cross-section measurement data between Lijin and Qing 7 from 1976 to 2006 were employed to address the erosion/deposition pattern of the mouth channels of the Huanghe Riv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water and sediment inputs since the Qingshuigou course was established.Results show that since then the incoming flow and sediment charges have remained in a lower level,with more sediment discharge concentrated in flooding season.Meantime,the accumulative dopositional amount in the main channel between Lijin and Qing 7 comes up to 3.15×108m3,of which 1.11×108m3 occur in flood season and 2.03×108m3 in dry season,and most sediment load deposit in the reach between CS7 and Qing 7.The scour and fill process of the mouth channel is rough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i.e.strong fill in flood season and slight adjustment in dry season(1976-1979),strong scour in flood season and strong fill in dry season(1981-1985),continuous fill in whole year(1986-1996),and scour in flood season and fill in dry season(1996-2006).There are two-year cycle of memory effects.Sediment amount of scour or fill in the mouth channel partially exhibited linear and/or rank correlation with runoff,sediment discharge and incoming sediment coefficient. However,water and sediment flux and water/sediment coefficients are not the major determinating foctor of the scour/fill pattern at the main channel.Flow and sedimentation process,riverbed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human activities play vital roles in scouring and filling process of the mouth channels.
-
-
[1] 庞家珍,司书亨.黄河河口演变初探[J].人民黄河,1979(3):30-42.[PAN Jiazhen,SI Shuheng.Preliminary study on evolution of the Huanghe river mouth[J].Yellow River,1979 (3):30-42.]
[2] 王恺忱.对《黄河河口演变初探》一文的讨论[J].人民黄河,1980(2):70-72.[WANG Kaichen.Discussion on "Preliminary study on evolution of the Huanghe river mouth"[J].Yellow River,1980 (2):70-72.]
[3] 师长兴,叶青超.黄河河口延伸对下游淤积影响的定量研究[J].科学通报,1996,41(15):1399-1401. [SHI Changxing,YE Qingchao.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sedimentation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with its mouth channel extension[J].Chinese Science Bulletin,1996,41(15):1399-1401.]
[4] 陈志清.50年代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的萎缩及其原因[J].地理研究,1995,14(3):74-81. [CHEN Zhiqing. Channel shrink and its cause at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since the1950's[J].Geographical Research,1995,14(3):74-81.]
[5] 张治昊,胡春宏.黄河口水沙变异及尾闾河道的萎缩响应[J].泥沙研究,2005(5):13-21.[ZHANG Zhihao,HU Chunhong.Variation of flow and sediment and atrophy response of tail channels in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J].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2005 (5):13-21.]
[6] 叶青超.黄河断流对三角洲环境的恶性影响[J].地理学报,1998,53(5):385-392. [YE Qingchao. Flow interruption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the Yellow River delta[J].Acta Geographica Sinica,1998,53(5):385-392.]
[7] 王开荣,黄海军,张永平.黄河清水沟流路河口尾闾段河床形态萎缩特征[J].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8,28(2):15-22. [WANG Kairong,HUANG Haijun,ZHANG Yongping.Shrinkage on riverbed form of the tail of Yellow River mouth in Qingshuigou course[J].Marine Geology and Quaternary Geology,2008,28(2):15-22.]
[8] 茹玉英,刘杰,朱岐武,等.黄河口水沙变异特征研究[J].人民黄河,2005,27(1):28-29 ,32.[RU Yuying,LI Jie,ZHU Qiwu,et al.Characteristics of Runoff and Sediment Vari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Mouth[J].Yellow River,2005,27(1):28-29,32.]
[9] 李松仕.对数皮尔逊Ⅲ型频率分布统计特性分析[J].水利学报,1985(5):40-48.[LI Songsi.Analysing of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og Person Ⅲ distribution[J].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1985 (5):40-48.]
[10] 许炯心.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黄河下游河道泥沙淤积宏观趋势研究[J].水利学报,2004(2):8-16.[XU Jiongxin.Tendency of sedimentation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influenced by human activities[J].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2004 (2):8-16.]
[11] 吴保生,申冠卿.来沙系数物理意义的探讨[J].人民黄河,2008,30(4):15-16. [WU Baosheng,SHEN Guanqing.Discussion on the physical meanings of incoming sediment coefficient[J].Yellow River,2008,30(4):15-16.]
[12] Shi C X,Zhang D L,You L Y.Sediment budget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China:the importance of dry bulk density and implications to understanding of sediment dispersal[J].Marine Geology,2003,199(1-2):13-25.
[13] 曹文洪.黄河下游水沙复杂变化与河床调整的关系[J].水利学报,2004(11):1-6.[CAO Wen-hong.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tion of sediment carrying flows and readjustmentof riverbed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J].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2004 (11):1-6.]
[14] 胡春宏,张治昊.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水沙过程响应关系[J].水科学进展,2009,20(2):209-214. [HU Chunhong,ZHANG Zhihao.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nk-full discharge in tail channel and the process of flow-sedi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J].Advances in Water Science,2009,20(2):209-214.]
[15] 陈建国,周文浩,孙平.论小浪底水库近期调水调沙在黄河下游河道冲刷中的作用[J].泥沙研究,2009(3):1-7.[CHEN Jianguo,ZHOU Wenhao,SUN Ping.Effects of water-sediment regulation by Xiaolangdi Reservoir on channel erosion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J].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2009 (3):1-7.]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686
- HTML全文浏览量: 224
- PDF下载量: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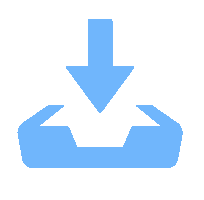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